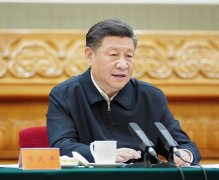此外, 2004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有把“传统”及“非传统”与“安全”连接起来的表述,分别为“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⑩]、“有效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11]。 在此,如果从语言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分析十六大《报告》中“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表述,及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的表述,可以发现它们都包含了“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两个短语;而如果再分析这两个短语,对它们进行断句,那么则可以把它们分别表达为“传统(的)||安全威胁的||因素”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的||因素”。由于这里的“安全威胁”其实就是“对安全的威胁”,所以如上两个短语可以分别翻译为“威胁安全的传统因素”和“威胁安全的非传统因素”。由此来看,“传统”和“非传统”在此修饰和限定是“因素”,而非“安全”,由此构成的概念是“传统的威胁因素”和“非传统的威胁因素”,或者是“传统因素”和“非传统因素”,而绝非“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当然,如上《报告》和《决定》的“威胁因素”,完全可以简化为“威胁”。正因如此,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之后不久,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以及2007年十七大《报告》和2012年十八大《报告》,相应表述中没有了“因素”地二字,分别成了“有效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12]和“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13][14]。 这样更为简洁的表述,更明确地显示出,“传统”和“非传统”修饰和限定的并非“安全”,而是“威胁”,由此形成的概念不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而是“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 由于篇幅限制,我们这里不再详细分析中央政府(国务院)报告在这段时间内的发生的相应变化和相关表述的准确运用,但结论却与上述对中共中央报告的分析完全一致。 这就使我们不能不问一句: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在语言文字方面也极具权威性的“中央文件”,把相关问题在事实上表述为“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而从来没有出现独立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表述呢? 我们认为,在已经大量而深入阐述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时,这些“中央文件”之所以没有用“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表述,并不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安全问题需要进行阐述,而很可能是因为这些权威文本的起草者和审阅者经过反复讨论、字斟句酌后,从汉语习惯和逻辑关系的角度,否定了国内大众传媒和学术论著中广泛存在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个语词,而采用了合乎汉语语法和普通逻辑的表达——“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毫无疑问,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在语言表达方面具有权威性的如上一些文本,对于安全和国家安全相关问题的如上表述,以及相应的理论概括,如果换作是某些学术论著,很可能会用甚至必然会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这种情况证明,这些“中央文件”是在有意避免和排除社会上及学术界已经广泛流行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这样的汉语表达,而这样做的原因,则是因为这些文本的起草者和审阅者认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汉语中是不正确(起码是不准确)的表达。我们完全可以将此作为旁证,来加强我们长期以来的直觉和观点:“非传统安全”一词(及相应的“传统安全”一词)在汉语中是不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