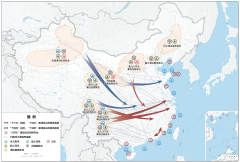更重要的是,两者的起步经费动辄20亿,相比于十五年花了不过8亿的龙芯,引进派弹药充足。兆芯成立两年后便实现了量产,卖了一万多套。海光2020年上半年营收2.7亿,净利润6000多万。 引进路线看起来立竿见影,却有一个致命的风险——国际局势的变化。 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一直在潜水《华尔街日报》突然给海光扣上了一顶“军方背景”的帽子。同年,海光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AMD随之宣布不再授权新一代Zen架构。从威盛那里买到专利的兆芯,也早收到了英特尔的警告:不要越过雷区。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相比当初的风雨飘摇,此时的AMD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死亡之谷,不再需要外援输血。况且,在湾区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AMD的芯片被用来为美国的核威慑提供动力。孰轻孰重,AMD自知。 “拿来主义”的路线,最终还是被证明存在根本缺陷。一直以来,大陆的x86人才极为薄弱,“拿来主义”能否进化到“吸收创新”,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只能停留在对x86硬件层面的拷贝与粘贴,那么很难深入地去搞研发,并且满足高安保级别和消费者市场的需求。 这种对于x86架构吸收的吃力,可以从兆芯管窥一二。2010年,威盛把x86带到了上海,技术负责人带着几百号人闷在小黑屋里,光是CPU核的源代码就看了两年,最终才弄懂。兆芯开始搞CPU后,四五百人的研发团队,倾力攻坚三四年,也只是维持了一个半CPU项目的开发,x86繁重的历史包袱,是“吸收创新”的巨大拖累。 全自主,需要从底层开始,几无可能;引进x86架构,却也面临被断供、无法更新的担忧。国产CPU的下一步,不得不回到最本源的问题:生态。
生态摸索 对于国产CPU来说,最好的老师始终是英特尔。不同之处在于,引进派采取“进口”拿来的思路,要在中国复制一个英特尔的国产化镜像,保证产业链的供应安全。而自主派需要做的,是学习英特尔在历史上的打法,最终形成一个在技术上不依赖外部供应的产业链。 简而言之,引进派学形,自主派学神。 另一方面,学英特尔不是问题,但学哪一年的英特尔是个大问题——所有采购单位遇到龙芯,都会提出一个直击灵魂深处的问题: 你们离英特尔有多远? 在带领龙芯经历了“大炼多核”的惨败后,胡伟武逐渐想明白:国产CPU应该学习的不是现在的英特尔,而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特尔:单扛众多竞争对手,利用“人民战争”打赢市场之战的革命者。 1985年,英特尔在DRAM市场被日本厂商群殴,CEO格鲁夫力排众议,集中转向彼时的“非主流市场”:应用于个人电脑的CPU。起初,英特尔在技术上处于劣势,但采取了三个策略: (1)从低端市场做起,造出好用的CPU,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2)保持向前兼容,虽然背上了历史包袱,但能够笼络一大批忠诚客户;(3)开放x86架构,制定外围标准,在产业链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动群众斗地主。 这三大策略,即是英特尔完成从电脑到服务器CPU统一战争的屠龙术。领悟到英特尔的致胜秘诀,从2012年开始,龙芯采取了三步走战略: 首先从嵌入式CPU着手,把龙芯应用到门锁、学习机和卫星上面。这些场景本来就是MIPS架构的天然场景,保证了现金流;然后中止多核研发,专注把单核性能做上去,这对普通用户的日常使用非常关键,也保证龙芯测试的时候不会拉胯;最后主动团结一切能团结的系统商、软件商和ODM工厂,像服务员一样服务好他们。 三步走逐渐取得成效,龙芯在2015年营收破亿,初步盈亏平衡。度过了鬼门关后,胡伟武发现,对于几乎没有独自建立过现代信息生态的中国人来说,国产CPU的生态工作千头万绪,只能参照另外一个学习对象,苹果。 在英特尔的世纪商战后,苹果实际上继承了其衣钵,但苹果的自研芯片之路其实也面临着两个特殊的难题:其一,从最上层的应用到最底层的芯片,其中层峦叠嶂,哪些是四两拨千斤的抓手?其二,苹果自研ARM芯片,一开始跑分极其难看,如果芯片拖了后腿,怎么保证终端产品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