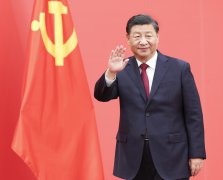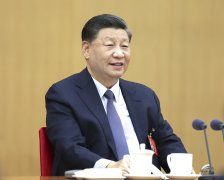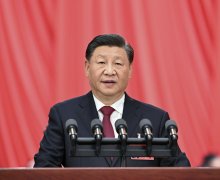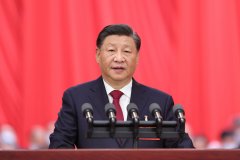按照往常,小时工出价到30元一个小时,招工会相对容易,但是11月7、8日两天林涛在四个500人的群里发了招工信息,只有10多个人表示了报名意愿。报名的人中,大多是八月高峰期没有进入富士康工作的人,年龄集中在30岁左右。这让林涛觉得,疫情之下,30块一小时的费用,“不够吸引人。” 富士康疫情控制住了吗?报名后能否健康工作?这是所有报名者关心的话题。 小梅在视频中解释,报名成功后,他们将进入预招工的统计名单,入职时间确定后,个人先完成一次核酸检测,然后进入当地的免费隔离点,隔离3天,三天三检,在阴性的情况下,统一乘坐大巴,点对点送到富士康,在厂区内闭环工作。  “中途可能会有人动摇。”袁飞也在富士康工作了11年,这两天他拉来了20多人。听完政策解释后,一些人会动摇,袁飞也不“硬劝”,他选择理解。 疫情之后的招工,流程更加复杂,疫情前的程序是,用身份证录入系统,面试,入职。疫情后对行程码,行程轨迹,户籍地,手机号是否为实名认证等信息都需要精准核实。 2020年春,全国疫情暴发,袁飞是春节后第一批到达厂区的员工,“去公司的时候整个区域就没有几个人。”他和同事一起合力统计工作人员的信息,核实无法上班的原因,是被封控,还是因为交通等问题。 也是在那个阶段,作为少数在厂区的人,袁飞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介绍富士康内部的工作情况,直播当天涌入的人数超出他的期待。在入职9年之后,他加入招工行列。 进入富士康 任凯与富士康的连接从学生时代开始。 2011年,任凯大一,富士康郑州园区开始招工。 乘着这股东风,任凯大一寒假的时候就进厂当学生工,在富士康拧螺丝,那时候iPhone 4大卖,一部苹果手机五六千元,任凯打工一个月工资只有3000多元。当时他的打工感受是,“这辈子一定要好好努力呀,你生产这个东西,可是最后却买不起”。 郑州富士康在当地拥有三个厂区,分别是郑州航空港厂区、经开区厂区、中牟县厂区。而此次疫情的中心是航空港厂区,在三个厂区中地位突出。航空港厂区面积560万平方米,不仅仅是郑州富士康3个厂区里最大的一个,也是富士康全球所有工厂里最大的一个。生产高峰期时有多达35万工人,承担了全球约一半苹果手机的组装工作。 当时任凯身边的郑州大学生纷纷进厂打工,富士康的岗位需求大约在每年一万人左右,“但是河南想进富士康打工的学生可能有两三万人”,学生工供大于求。 任凯瞄准商机,和一家劳务公司合作,成为他们的学生代理,专门向富士康输送学生工。他在学校里发传单,立一个“富士康招工”的牌子,给学生介绍富士康的工作。大一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招到了60多个人和他一起进厂,每招一个人,他可以得到150元的提成。毕业时,他已经有一笔上十万的存款了。 任凯的成功,与当时的招工模式分不开。富士康入驻郑州时,河南省政府除了给富士康提供土地、税收等利益让渡之外,对其最急需的劳动力推行了“自上而下”的招工模式。 河南大学副教授陈肖飞在《劳动力视角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战略耦合机制——以富士康郑州投资为例》一文中称,2011年郑州富士康开始招工,那一年也是河南省农业人口省内转移人数高于省外输出人数的拐点。 初期,河南省政府将招工任务分配给了河南省各地级市政府,任务逐级下放,平均每个乡镇都需要招募30-50名工人去富士康工作,甚至还将招工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政府工作的重要参照标准。 除了按照行政层级划分招工任务,政府还将招聘任务分配到一些市场职业中介机构。除此之外,河南省教育厅要求省内各地的职业学校动员组织二、三年级的学生到富士康进行实习,以保证有充足的高素质员工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