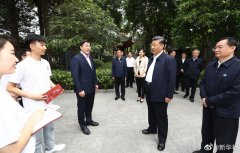山路费车,这已经是麦尔干换的第三辆车了。 司占伟 摄 山路费车,车辆的损耗大大增加,寿命缩短到五六年。这已经是麦尔干换的第三辆车了,可他全不在意。每个月他都会往各个山口的执勤点送人和物资,少则十几趟,多的时候如疫情期间,每天至少一趟。路途遥远,义务护边员的补贴只够加油,麦尔干却乐在其中。 每次出发前,母亲都会捧着馕站在门口,一边把馕递给他一边嘱咐:“路上小心,别饿着。”出发后,这个画面会长久地浮现在麦尔干的脑海里,让他感到温暖和心安。 从航拍器中俯瞰,我们眼前这些巨大山脉犹如一张张风干的褐色树叶标本,叶脉上落了白霜的部分就是一座座雪山之巅。在那些颜色深浅不一的脉络之间,最大海拔落差能达到6000多米。我们的车就像一只小虫,爬过一片树叶、然后又一片树叶,最后终于在两座平房前停了下来。一张张质朴的笑脸从屋内迎了出来,这里是距离乡镇最近的执勤房。
从飞机上俯瞰帕米尔高原的山脉。 雷册渊 摄 执勤房里,一张炕席、一个回风炉、一套餐桌椅、一部电话机,陈设简单、整洁。开口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边境上的普通牧民,现在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义务护边员。
巡边途中的义务护边员。 雷册渊 摄 46岁的买买提居马·努尔麦麦提是这里护边最久的人,巡边、护边20年;戈丹·塔西马麦提以前住在县里,女儿出嫁后,闲不住的她申请上山护边,她的嘴里镶着两颗金色的牙齿,笑起来格外明亮;50岁的艾尼瓦尔是布茹玛汗大妈的邻居,从小听大妈讲故事,6年前加入了义务护边的队伍,有次在山上被暴风雪困住回不来,生起篝火蹦了一夜,既抗冻,又防野兽。 义务护边队伍里最多的还是父子和夫妻。阿卜杜赛依提·吾如孜马麦提护边近20年,4年前光荣入党,见我们的时候,胸前别着崭新的党员徽章,2017年,他的妻子也加入了义务护边;特尼白克·拖哈拖荪同样和妻子一起护边,35年前,他的父亲曾骑着毛驴走在护边小路上;哈力别克·扎尔普别克有两个女儿,他希望自己能够支持她们好好读书,走出大山……
27岁的古力司坦·库尔曼白克也是吉根乡的义务护边员之一。 司占伟 摄 多年来,布茹玛汗大妈义务护边的事迹在西陲高原上传颂,越来越多的牧民在放牧时主动承担起义务巡边、护边的任务。2017年,乌恰县进一步完善义务护边员制度,改善护边牧民的生活条件。 有人说:“在这里,每一座毡房都是一个流动的哨所,每一个牧民就是一座活着的界碑。”在这里,跟任何一个人聊上一会儿,你都能收获一份最质朴的热爱,这种情感关于故土,关于祖国。 去最远的山口,要驱车100多公里,抵达脉络深处的山脚,再徒步登山两小时才能到达。27岁的古力司坦·库尔曼白克从吉根乡考入武汉大学,又回到了家乡,成为一名义务护边员。在那个山口,他和同伴们仿照布茹玛汗大妈的样子,刻了一块“中国石”,还用油漆描了红。他们种了几棵树,省下洗脸水浇灌它们,第二年竟然真的发出了嫩芽……“执勤房门口有绿树、有‘中国石’,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满山丰茂的牧草和牛羊。守在那里,真的就像守护着自己的家。”
4月,帕米尔高原上正在开化的冰河。 雷册渊 摄 我们走出执勤房时,日影西斜,门前,冰川融水汇聚成一条大河,奔腾向前,仿佛孕育着“铁马冰河入梦来”式的豪情壮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