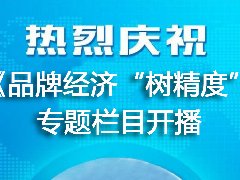一、媒体素养的内涵演变:从“防御”到“参与” 媒体素养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和深化。早期,它主要强调对信息筛选与分析的基本能力;而在融媒体时代,媒体素养则涵盖了更广泛的内容,包括对数字技术和平台规则的理解、跨文化传播意识以及批判性思维等多方面内容。在媒体融合环境下,各种媒介形式相互融合,信息来源多样化且复杂化,这使得公众需要更高的辨别能力和判断力来区分真伪,避免被误导。 “媒体素养”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英国学者利维斯提出通过教育抵御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侵蚀,强调培养公众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性思维。这一阶段的媒体素养带有鲜明的“保护主义”色彩,核心是教导公众识别并抵制媒介中的负面信息。随着媒介技术的迭代,媒体素养的内涵逐步扩展。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将其定义为“面对媒介信息时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创造和思辨能力”,这一概念突破了被动防御的框架,转向主动参与。 在融媒体时代,媒体素养的内涵进一步深化。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使媒介素养需涵盖“智能媒介”素养,即适应算法推荐、数据挖掘等技术的能力。对媒体人而言,媒体素养要求不仅限于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技能,还需具备对技术伦理的敏感度、对用户需求的洞察力,以及对公共价值的坚守。山西省朔州市融媒体中心紧跟智能化的步伐,探索出了培养“一岗多能”人才的路径,既要求编辑兼记者、播音员兼制作,又强调政治素质与职业道德的同步提升,充分体现了融媒体环境下素养要求的综合性。 二、融媒体时代的新挑战:技术赋能与媒体伦理风险并存 融媒体时代的技术进步无疑为信息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媒体行业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挑战。人工智能写作工具虽然大幅提高了新闻生产的效率,却容易导致内容趋于同质化,缺乏个性化表达和深层次的人文关怀。与此同时,算法推荐机制虽然能够根据用户的浏览习惯推送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但长期使用可能会强化“信息茧房”效应,使人们局限于狭隘教条的认知框架之中,难以接触到多样化的观点和信息。 除了上述问题外,诸如深度伪造(Deepfakes)技术类的广泛应用更是加剧了虚假信息传播的风险。这种技术可以轻松生成高度逼真的伪造视频或音频,使得辨别真假变得更加困难。大量经过深度伪造处理的信息在网络上流传,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困惑,同时对社会稳定和公共信任造成严重威胁。 针对这些挑战,媒体人必须具备两方面的关键能力。一方面,他们需要掌握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运用大数据技术深入分析用户行为模式,从而创造出更具吸引力和互动性的新闻作品;另一方面,则是要具备较强的伦理意识,特别是在处理敏感话题或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时,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流量至上主义倾向。有美国学者指出,媒体素养的核心在于学会全面评估信息及其来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这在当前高度依赖技术辅助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媒体从业者应当将传统的经验直觉与现代科学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基于证据的验证流程,以确保所发布的每一条消息都是准确可靠的。所以媒体机构和个人都必须积极适应变化,不断提升自身素质,确保信息传播既高效又负责任。 三、媒体素养的核心要素:政治性、专业性与公共性 1. 政治素质,融媒体时代的“定盘星” 融媒体中心作为重要的基层主流舆论阵地,肩负着引导社会舆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使命,因此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至关重要。要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融媒党建讲堂,强化全体工作人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将党性修养贯穿于新闻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这种政治素养不仅体现在对国家政策的精准解读上,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把握正确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