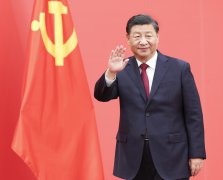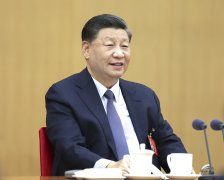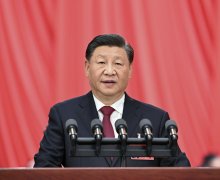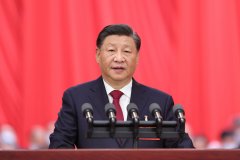无论是在古代安全状态下,还是在现代不安全状态下,包括生物资源安全和生物生态安全两种情况的生物安全,其具体内容都非常丰富,例如生物物种安全、生物多样性安全、生物基因安全、植物种子安全、珍稀动物安全等。对此不作深入讨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生物物种安全、生物多样性安全,还是植物种子安全、珍稀动物安全,以及生物基因安全,在人类安全体系中,包括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中,都是对人无害的安全,是至少对人无害的生物及其对人无害状态下的安全,而不是超越人类生存发展需要和安全的绝对安全。为此,早已存在的动植物保护,以及当前人们强调的生物安全保障,都是有限的相对保护和保障,而不是无限的绝对保护与保障。对于威胁危害人类生存发展的生物来说,人类就不会让它们安全,也不应该去保护和保障它们的安全。 不该安全的生物:生物威胁及其防范化解 人类离不开生物,并不是说人类离不开任何一种生物。人类在离不开某些特定生物的同时,却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离开另外一些生物,甚至还必须警惕、防范另外一些生物,例如致病的细菌和病毒、伤害人类性命的豺狼虎豹、伤害人类生活所需家畜和其他生物的生物。在人类安全体系及相应的生物伦理关系和生物法律关系中,有些生物不是应该保护的生物,也不是“生物安全”概念能够合理指向的生物。与这些有害生物相应的合理概念,不是“安全”和“生物安全”,而是“威胁”和“生物威胁”。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物资源的相对充足和生物生态的相对良好,人类不会关注和重视生物安全,甚至根本就忽略了生物安全。相反,由于生物威胁的明显存在和时常发生,早期人类对生物威胁则一直比较重视甚至是非常重视。 早期人类虽然不可能认识到所有的生物威胁,或者说不可能认识到威胁人类安全和发展的所有生物,但却能够注意到也必然会重视那些明显存在的生物威胁,例如毒蛇猛兽对人类生命安全的威胁和危害、某些野生动物对人类家养牲畜的威胁和危害,还有毒株杂草对人类自身生命和所种粮棉植物的威胁和危害。在我国农村广大区域,历史上就发生过不少婴幼儿甚至成人被狼叼走和吃掉的悲剧性事件,这一点在鲁迅的《祝福》和陈忠实的《白鹿原》中都有描写。再如,面对各种“害虫”对农作物的威胁和危害,人类早期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有在现代科技推出各种农药后,才得到比较有效的防范和化解(农药副作用是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害虫”与“益虫”的划分,非常明显是从人类视角出发的,是基于对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关系而作出的。“益虫”应该安全,需要保护;“害虫”不该安全,需要消灭。如果说这是一种“人类中心论”,那么人类可能跳不出“人类中心论”,问题只在于“极端人类中心论”和“温和人类中心论”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还是从人类出发、以人类为尺度考虑和衡量的。至于早期人类还无法明确认识的以细菌病毒为主的某些微生物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和危害,长期处于早期人类自然目力及前科学时代经验和思想之中,人们常常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实际伤害,因而也不能不努力用想象填补经验和知识的空白,设想出各种神秘力量来进行解释,并力图通过同样神秘的巫术等原始手段来防范和化解这些神秘莫测的威胁和危害。 人类认识和防范化解各种生物威胁的历史进程,总体上是不断上升前进的。随着经验的不断丰富,知识的不断积累,特别是现代科学理论及科学技术的出现及迅速发展,有害生物及生物有害性方面对人类的威胁危害程度相应地不断减弱和下降。曾几何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极大提升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自信,人们不仅相信自然的秘密即将被现代科学理论彻底揭开,而且更相信现代科学技术将使人类无所不能、无往不胜。在世纪之交前后构建自己的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时,笔者根据历史事实,把“虫”和“疫”列在了威胁国家安全的“天灾”之中,但现代科技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医疗卫生技术的空前发达,使一些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已使“虫”和“疫”不再可能威胁人类安全和国家安全。当时只能说,在国家安全学理论中列入“虫”“疫”之类的生物威胁,是对历史事实的概括,是具有普遍性和普适性的国家安全学理论需要概括进来的历史内容。然而无情的事实是,非典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证明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及无知、无奈和无助。当然,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与人在自然面前的伟大一样,都是相对的。同样,面对疫情在内的种种自然灾害,人类的无知、无奈和无助,与人类的有知、有为和有力一样,也都是相对的。这就是说,人类一方面越来越多地了解和揭示了自然及生物的各种秘密,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控制和化解着自然及生物的各种威胁,同时也还存在着许多人类不了解、不知道的自然现象、生物现象,存在着许多人类难以完全控制和化解的自然威胁、生物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