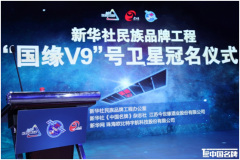第三,具有制度弹性与可调适性。制度的长期性与制度弹性并不冲突,在制度目标和战略长期稳定的情况下,具体制度不能过于僵化、脱离现实。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鲜明特征是“问题导向型”政党,执政过程中的政策拟定与选择,能以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薄弱环节、具体目标为中心,根据问题与目标不断调整战略与政策,根据不同问题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少西方学者特别看重这一点,把强调问题意识、实践导向的中国共产党称为一个能够不断“自我调适”的“弹性”政党,并以此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第四,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除制度僵化外,西方国家还存在“家族制复辟”的倾向,制度仅代表部分特权阶层、精英群体的利益。实际上,不仅如此,就其政党本质而言它就仅具有部分代表性,西方不同政党代表着不同群体或阶层利益,其执政后的政策自然也会如此。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它是大众代表型政党,其性质决定了它领导下的制度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正义性。 第五,具有约束与激励并举的制度效应。中国共产党内部拥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制度,这是其治国理政能力的制度保证,也是整个组织初心与使命、先进性与纯洁性的重要保障。但同时制度也有激励的维度,通过学习制度、竞争制度、提拔制度等,激励干部干事创业、完成治理任务。 有效治理体制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效治理体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首先,从传统看,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决定国家的“整合任务”优先,有效整合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传统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一直是“如何将一个大国整合与组织起来”。上古三代之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面临的首要问题即是秩序重建、国家整合。秦国通过强力完成了这一任务,之后虽有变迁,但实质上“二千年皆行秦制”。维系大一统帝国是传统中国治理的首要任务,特别是历朝历代持续面对边疆外患,基本一直借助“中央集权”加“周边相对自治”的多元复合帝国模式维系一统局面。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大动乱之后,无论隋唐还是宋明,其首要目标仍是再度统一、帝国重建、秩序稳定、长治久安。近代中国亦如此,清末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传统中国彻底解体,整个体系系统性失败,面对这千年未有之变局,救亡图存成了根本任务,整合任务更加凸显。真正完成近代中国重新整合的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国民党等各种政治势力均无力完成的组织社会这一基本任务。 其次,从现实看,当代中国实现有效治理,必须有能够凝聚各方面力量的领导核心。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语境是“复杂中国”的国家治理。“复杂中国”至少包含四个维度,其一,巨型国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世界上具备如此地理、人口等客观要素的国家并不多。其二,多元社会。这里的多元,指的是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习俗多元、区域差异多元、发展阶段多元,还叠加了现代社会的观念多元和利益多元。其三,国际竞争激励。国际领域客观上还存在着弱肉强食的半丛林化自然状态,一个地缘位置重要、文化迥异、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正在迅速发展壮大,即便自身安心发展,也必然遭致干扰、挑战和威胁。其四,现代转型。中国依旧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后工业社会转型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心任务仍是追赶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要言之,“复杂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的根本任务是:追赶条件下多元巨型社会的有效治理。 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治。现代政治,大众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就是政党,政党都是政治活动的主角。但是,不同国家的情况并不一样。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通过自我牺牲在历史中获得了人民的认可。从现实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新中国,取得了不容否认、举世瞩目的治理成就,进一步巩固了人民的认可,也彰显了党的执政能力。就政党类型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兼容并蓄型”政党,既有广泛的代表性,又有强有力的大众动员能力;既有利益整合能力,又有政策转化能力,还有象征性认同功能。这些因素综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深厚基础,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广泛认同,为实现有效治理注入了强大力量。“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有效治理“现代化”的不懈追求,将确保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稳健前行。 |